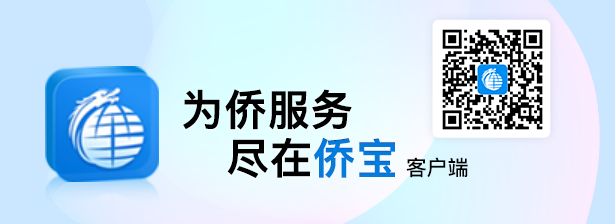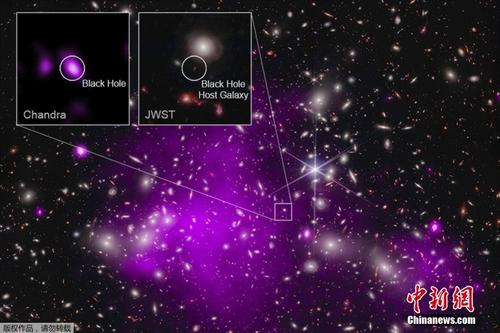古舊書之城蘇黎世:大街小巷中隱藏著無數(shù)“寶藏”
古舊書之城蘇黎世
文/曹然
本文首發(fā)于總第885期《中國新聞周刊》
蘇黎世的名聲常與“平庸”掛鉤,但淘書客們的觀點顯然不同。
瑞士人愛古籍和舊書,。蘇黎世國立博物館評價善本時說:“有些東西誕生就是為了永恒,?!碧K黎世樸素的大街小巷中,,就隱藏著無數(shù)這樣的寶藏,。
由西方36個國家的1800余家古舊書店組成的國際古書商聯(lián)盟(ILAB),,總部設(shè)在瑞士日內(nèi)瓦。蘇黎世擁有16家成員,,不僅超過日內(nèi)瓦和其他瑞士城市的總和,,在國際上也僅次于巴黎、倫敦,、紐約和柏林這四座人口超過蘇黎世數(shù)倍至數(shù)十倍的大都會,。這使得蘇黎世成為歐洲大陸頂尖古舊書店最多的城市之一,傲視法蘭克福,、漢堡,、維也納、羅馬,、里昂等環(huán)繞周圍的歷史文化名城,。

與歐洲常見的沿街店鋪不同,蘇黎世街邊舊書店往往占地面積較大,有兩層或多進(jìn)房屋,。長期和平的環(huán)境讓商人們沒有遷移的煩惱,,空間與時間的富裕令店主們得以從容創(chuàng)造自己的天地。于是,,讀書人鐘愛的古舊的木制書柜,、吱呀作響的樓梯、簡約雕刻的閣樓欄桿成了這里舊書店的標(biāo)配,。攤開的大型畫冊放在中世紀(jì)風(fēng)格的傾斜讀寫臺上,,背后是整柜的皮面精裝書。這些小店又多兼營古物與繪畫,,十九世紀(jì)的風(fēng)景,、人像銅版畫、油彩畫與各式雕像參差于書柜間,,雖然不見得珍稀,,但總給人一種身處貴族莊園書房的感覺。
蘇黎世美術(shù)館旁一座羅馬式大樓里,,一家門面不大,、甚至有些灰頭土臉的書店夾雜在一片私人銀行中間。梅爾基奧爾書店不是ILAB的成員,,甚至不被谷歌地圖所標(biāo)注,,但推開厚重的小門,里面是令人驚嘆的浩大工程:從墻根一直堆到高挑天花板的舊書把不小的店面塞得滿滿當(dāng)當(dāng),,通向書庫的樓梯兩側(cè)也密排書柜,,釘著銘牌的木柜腳下還有層層摞起的古舊繪畫,每張畫的背面都工整記錄著畫家和年代等信息,,還有源流考證和出售編碼,。幾冊十八世紀(jì)的革命宣傳小冊子被粗暴地用夾子掛在書柜外,柜上無序地排列著歐洲的石雕,、非洲風(fēng)格的木雕,、東方的佛像等裝飾品。這些雕像表情各異,,似乎都在發(fā)出驚嘆,。
恰當(dāng)?shù)姆诸愂菚甑曛鱾円詾楹赖墓Ψ颉LK黎世的博物館學(xué)家曾說:“給文物分類是困難的,,但一旦掌握了分類,,就獲得了通往古代的門票?!边@與中國歷代學(xué)人注重版本目錄之學(xué)是同樣道理,。
梅爾基奧爾書店顯然拿到了通向中古西方世界的“門票”,。被書山掩蓋的柜臺上有一本家族記錄,名字大略是《一家人和他們的兩萬冊古籍》,。蒼老的店主不知是第幾代傳人,,他抬頭瞥了眼來客,又靜靜擺弄起手上的古籍,。
“有沒有中國的書呢,?”老人抬起頭,穿過兩側(cè)與他齊肩的書堆,,來到一個塞滿十九世紀(jì)精裝書的木柜前,,手掌隨意撫過幾冊舊書,就準(zhǔn)確抽出了他的目標(biāo):“你看看這個,,這個是不是中文,?”
英文圖冊上三個日語中的漢字映入眼簾。熟稔西方各國文化的店主似乎分不清這本典型日本風(fēng)格的畫冊到底屬于東方的哪種文明,。
“這是日本的,。這幾個字,,可以說是漢字,,但日文也是用的?!甭犃酥袊櫩蛡儺惪谕暤幕卮?,老人并不甘心,又翻了幾頁,,直到他看到一張和服女子的畫像:“哦,,這是日本的,日本的,?!彼钢鴪D,一副恍然大悟而又有些失落的樣子,。
如果逛厭了繁華而無趣的街道,,從蘇黎世大教堂向東隨意拐上一條民居間的小道,斷頭路快到盡頭時,,一家窗邊陳列著奧運(yùn)會獎牌和英超球衣的小店會突然閃現(xiàn),。不身臨其境,人們很難想象瑞士乃至歐洲最有名的體育專題舊書店之一就躲在蘇黎世如此偏僻的小角落里,。
與許多蘇黎世同行不同,,戈蒙德體育古舊書店沒有設(shè)英語區(qū)。汽車運(yùn)動類藏品的展柜下躺著幾冊英國經(jīng)典賽車品牌的舊宣傳冊和上世紀(jì)六七十年代一級方程式比賽“死亡歲月”期間的國際汽聯(lián)賽事規(guī)則,。書架上,,法拉利,、保時捷、蓮花的車隊簡介,、賽手簽名自存的賽車維修手冊,、車隊小規(guī)模印刷的賽車手傳記鱗次櫛比。一切都顯示出,,偏居蘇黎世小巷的這座書店其實是“體育世界的中心”,。
不少圖書的標(biāo)記和題識告訴我們,它們曾經(jīng)是一些專業(yè)或業(yè)余運(yùn)動員的珍藏,,歷經(jīng)歲月后聚集在這一片小店里,。而它們的主人,或許已經(jīng)帶著對體育事業(yè)的熱愛離世了,。
“我們這里有幾乎所有運(yùn)動門類的書籍,。”店主格雷戈里自豪地對顧客們說,。這位曾在蘇黎世著名的皮特·彼得古書店工作的瑞士人和他的許多同胞一樣能說英,、法、德,、西四種語言,,在藏品分類上也是一把好手。書柜間錯落有致地劃分出獎牌,、照片,、唱片、海報,、衣物,、旗幟、卡片等體育收藏獨有的門類,。
在店內(nèi)擺放中國武術(shù),、跆拳道、柔道書籍的專區(qū),,我找到了一本蘇黎世難得一見的中國舊書——一冊1969年出版的《中國歷代體育活動分類史料圖片選集》,。“這本書就是在這里等你的,!”格雷戈里興奮地說,。
這本書是中國近現(xiàn)代著名體育史學(xué)者吳文忠先生以英文簽贈給瑞士波恩大學(xué)體育學(xué)院前院長克萊門特·維爾特的,1975年又被維爾特送給了剛剛成立的瑞士體育博物館,,歷經(jīng)波折后棲身于大量日本武術(shù)文獻(xiàn)之間,。整整半個世紀(jì)后,在這座被貼滿“金融”“購物”和“科技”標(biāo)簽的城市里,,被我這個中國讀者所淘到,。
梅爾基奧爾老店與戈蒙德書店并非這座文化古城中最有名的書鋪,,但它們代表了當(dāng)代蘇黎世書商們的兩種風(fēng)格:一種恪守家族式經(jīng)營,蝸居書山,,隨緣遇客,;另一種則汲取現(xiàn)代書店經(jīng)營模式,甚至建立多語種網(wǎng)站,,做起全球的生意,。后者造就了今日蘇黎世“古舊書重鎮(zhèn)”的地位,而前者則繼承著歐洲古書商們的傳統(tǒng),。
在這座人人行事如鐘表般精確的城市里,,這些舊書店的存在讓人感到,有些地方的時間被撥慢了,。在這里,,店主與其藏品們躲在幽巷小門之后,靜靜地等待有緣之人,。
《中國新聞周刊》2019年第3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wù)經(jīng)書面授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