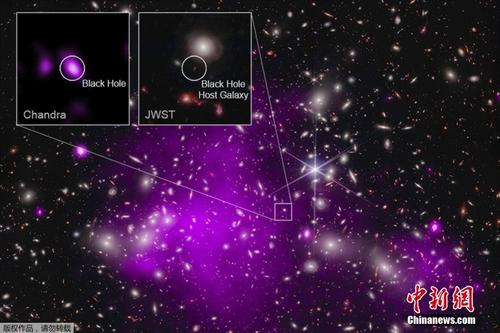當(dāng)代昆曲上海首演 中英文原著臺(tái)詞“亂入”(圖)
 參與互動(dòng)
參與互動(dòng)
一邊是有著600年文化沉淀的昆曲,一邊是莎士比亞400多年前“生存還是死亡”的終極拷問(wèn),,上海張軍昆曲藝術(shù)中心將二者結(jié)合在一部名為《我,,哈姆雷特》的當(dāng)代昆曲之中,。該劇作為第十八屆中國(guó)上海國(guó)際藝術(shù)節(jié)委約作品,,在昨天(13日)首演于中華藝術(shù)宮,。東方的手眼身法步,,演繹西方戲劇經(jīng)典,?出品人兼主演張軍,,以一場(chǎng)長(zhǎng)達(dá)75分鐘的獨(dú)角戲試圖讓東西方文化同臺(tái)對(duì)話。
戲還未上演,舞臺(tái)上升起薄霧,,一支4人制的樂(lè)隊(duì)奏響悠揚(yáng)樂(lè)音,間以低聲吟唱。身著藍(lán)衣的張軍道出“哪個(gè)哀吟,,驚落流星”的感慨。劇中,,他一會(huì)是帶著髯口的已故父王,,一會(huì)是黏上胡須的掘墓人,,一會(huì)是身披柔紗的奧菲利亞,不過(guò)更多的時(shí)候,,他就是躊躇猶疑的王子哈姆雷特,。
沒(méi)有幕間休息,張軍在舞臺(tái)上通過(guò)少量道具,,和行當(dāng)變化完成多個(gè)角色轉(zhuǎn)化,。比如,掘墓人以丑行應(yīng)工,,講一口蘇白,;而奧菲利亞則是閨門旦,一段帶著哈姆雷特賞花的戲,,則是脫胎自《牡丹亭》中的《游園》一折,,編劇羅周還特別用了原作的一句經(jīng)典:“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
沒(méi)有下場(chǎng)的機(jī)會(huì),,張軍常常需要在一個(gè)蹲下轉(zhuǎn)身間完成人物變化。一場(chǎng)戲中他變身掘墓人時(shí),,需要在幾秒鐘內(nèi)完成吸汗,、喝水,、戴鼻卡、掛上腰包,、把袍襟扎進(jìn)腰間,、拎起酒壺等一系列動(dòng)作。張軍說(shuō):“既要通過(guò)標(biāo)志性的裝束,、身段,、唱腔的變化方便觀眾辨識(shí),同時(shí)希望動(dòng)作流暢不露痕跡,。比后臺(tái)的趕妝還要提心吊膽,。”
在音樂(lè)上,,該劇邀請(qǐng)作曲家金復(fù)載操刀運(yùn)用大提琴,、笛子等多種東西方樂(lè)器。而唱腔設(shè)計(jì)部分,,張軍請(qǐng)來(lái)老師顧兆琳把關(guān),,希望回歸昆曲正統(tǒng),比如父王亡魂企圖帶走哈姆雷特時(shí)演唱的《四門子》等曲牌都是傳統(tǒng)的昆曲曲牌,。
不過(guò),,帶給觀眾更大沖擊的,并非昆曲,,而是舞臺(tái)上更為現(xiàn)代,、西方的表達(dá)。沒(méi)了一桌二椅,,取而代之的是舞臺(tái)四周立起十?dāng)?shù)根高桿,,上面懸置一把椅子,有的坐著人偶,,有的則是空的,。在演出結(jié)尾,從椅子上方有幾股細(xì)沙傾瀉而下,,不知道還以為看的是當(dāng)代裝置藝術(shù)的展示,。臺(tái)詞上,在演出首尾,,還“亂入”了英文原著的臺(tái)詞,。而另一部分臺(tái)詞,又是以普通話念出,。
面對(duì)這些處理,,記者忍不住向主創(chuàng)發(fā)問(wèn):“不擔(dān)心這樣不夠昆曲嗎?”導(dǎo)演李小平解釋,,要的就是這種“亂”,,他希望用這種方式呈現(xiàn)當(dāng)下時(shí)代文化交錯(cuò)對(duì)話的“亂碼”感,。他說(shuō):“講一個(gè)完整的丹麥王子復(fù)仇的故事不是我們的第一目的,體現(xiàn)中西文化上的對(duì)話,,實(shí)踐中從作品內(nèi)涵到表現(xiàn)形式的沖撞與交融,,才是這個(gè)戲追求的真正意圖?!?/p>
盡管這部《我,,哈姆雷特》非常先鋒,可張軍更愿意將其定義為“當(dāng)代昆曲”而不是“實(shí)驗(yàn)昆曲”或者是“小劇場(chǎng)昆曲”,。時(shí)間往回?fù)芤稽c(diǎn),,這個(gè)“當(dāng)代”也被他用來(lái)定義《春江花月夜》。只是眼下,,不論是打破鏡框式舞臺(tái),還是舞美的當(dāng)代藝術(shù)色彩,,以及中英文對(duì)白,,都比 《春江花月夜》的步子邁得更大———在湯顯祖和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之際,《我,,哈姆雷特》與其說(shuō)是“400年來(lái)的舞臺(tái)拷問(wèn)”,,不如說(shuō)是當(dāng)代戲劇人“不得不面對(duì)的人生課題”。(黃啟哲)